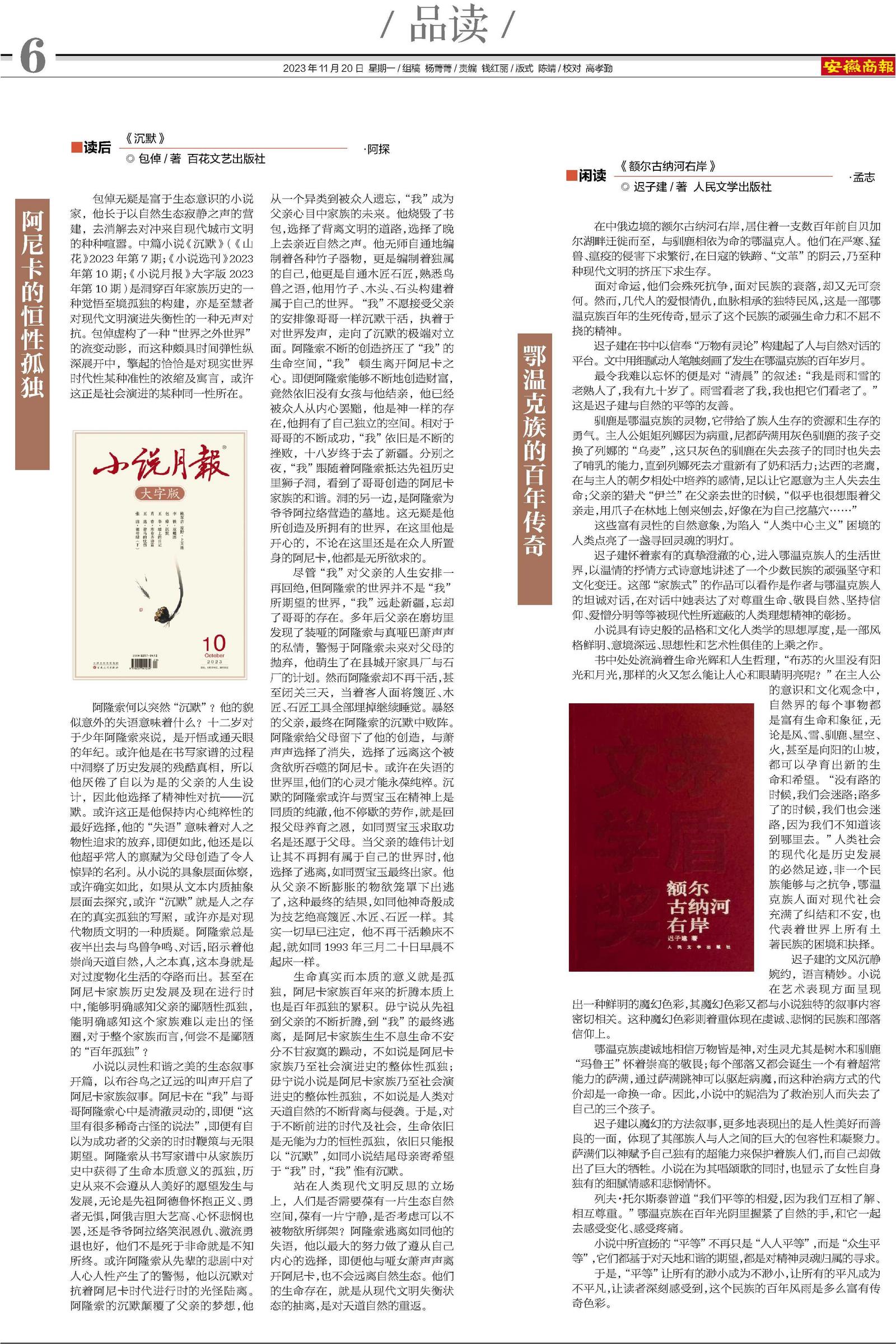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
·孟志
◎ 迟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面对命运,他们会殊死抗争,面对民族的衰落,却又无可奈何。然而,几代人的爱恨情仇,血脉相承的独特民风,这是一部鄂温克族百年的生死传奇,显示了这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迟子建在书中以信奉“万物有灵论”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对话的平台。文中用细腻动人笔触刻画了发生在鄂温克族的百年岁月。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便是对“清晨”的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的平等的友善。
驯鹿是鄂温克族的灵物,它带给了族人生存的资源和生存的勇气。主人公姐姐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的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在为自己挖墓穴……”
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意象,为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人类点亮了一盏寻回灵魂的明灯。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
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书中处处流淌着生命光辉和人生哲理,“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心和眼睛明亮呢?”在主人公的意识和文化观念中,自然界的每个事物都是富有生命和象征,无论是风、雪、驯鹿、星空、火,甚至是向阳的山坡,都可以孕育出新的生命和希望。“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足迹,非一个民族能够与之抗争,鄂温克族人面对现代社会充满了纠结和不安,也代表着世界上所有土著民族的困境和抉择。
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魔幻色彩,其魔幻色彩又都与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密切相关。这种魔幻色彩则着重体现在虔诚、悲悯的民族和部落信仰上。
鄂温克族虔诚地相信万物皆是神,对生灵尤其是树木和驯鹿“玛鲁王”怀着崇高的敬畏;每个部落又都会诞生一个有着超常能力的萨满,通过萨满跳神可以驱赶病魔,而这种治病方式的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因此,小说中的妮浩为了救治别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迟子建以魔幻的方法叙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人性美好而善良的一面,体现了其部族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萨满们以神赋予自己独有的超能力来保护着族人们,而自己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小说在为其唱颂歌的同时,也显示了女性自身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悲悯情怀。
列夫·托尔斯泰曾道“我们平等的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相互尊重。”鄂温克族在百年光阴里握紧了自然的手,和它一起去感受变化、感受疼痛。
小说中所宣扬的“平等”不再只是“人人平等”,而是“众生平等”,它们都基于对天地和谐的期望,都是对精神灵魂归属的寻求。
于是,“平等”让所有的渺小成为不渺小,让所有的平凡成为不平凡,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百年风雨是多么富有传奇色彩。